《塔洛》剧情介绍
孤儿塔洛牧羊维生,他是记忆世界的国王,记得所有的事情,但他却是真实生活的边缘人,没人记得他,连他的名字都忘记了,只唤他小辫子。直到他遇到理髮馆女孩,第一次被人记得,第一次爱,那就是存在的开始。塔洛开始一场爱情,很多惊奇,大多失望,见天地,望众生,然后回到自己。辫子失去了还会长回来,那关于这个世界呢?总是需要一次离开,然后才知道归来。 改编自导演万玛才旦短篇小说,聚焦藏人生活景况,以黑白影像粗粝质感勾勒出西藏大地的苍凉,更缩影这一代藏族青年的内心迷惘。在心灵的高原上壮游,以为走得那麽远,其实仍踌躇传统原生文化与现代文明间,欲离何曾离,云空未必空。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鬼妻我爱你偷心女盗乱世江湖:神兵决梦想成真凤凰谷磨坊亚美利加纳直击追捕现场第一季人海同游撒旦定居点海豚李卫当官娃娃屋情归新泽西女人如花夺命梦魇赞助商让子弹飞芒针星星的故乡灵能百分百Ⅲ女间谍龙套之王众神与将军小心肝儿一代宗师浪子燕青之好汉归来是非之地南瓜剪刀有泪尽情流
《塔洛》长篇影评
1 ) 《塔洛》魔方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变形记》开篇终其一生,弗朗兹·卡夫卡任性放纵自我意识,让灵魂流淌于布拉格的街巷之间。
若干年后,他笔下致力于拆解、颠覆的迥异世界,变成了东方一个抽离精准坐标与线性时间的另类寓言。
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某处草原,普通牧羊人塔洛塑造了一个同时容纳鲲鹏与蝉鸠的魔方。
魔方随意转动而不散开,潜行的规则是同色模块的整齐复原,然而混乱与错位,才是这个真实机械世界中最充满趣味的变数与奥秘。
在导演万玛才旦的镜头里,电影《塔洛》的魔方世界只有黑白两种颜色,世间最简单之色,涌动着最难辨析的运行逻辑。
黑白是平行的二元,也是边界的模糊,延伸着空间深处的意义,也消解时间的无始无尽。
黑白是对立的分明,也是阴阳的流转,是善恶、聪愚、明暗、纯杂、忠叛……的镜像互照。
牧羊人塔洛固守在魔方的一角,是自己精神王国的“独裁者”,他离群索居,从未打算进入那个复杂精巧但难以理解的结构性世界,也因此几乎无需向任何力量妥协。
但是某一天,转动的秩序规则终于发现并找到了他,这是一次毫无焦点的碰撞,塔洛不得不去证明自己作为塔洛的存在,而他所有能应对这一荒诞命题的经验,仅仅是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所作的演讲——《为人民服务》中关于死亡性质的判定。
塔洛一字不漏地背诵着这篇1944年的文章,并借此获得进入了魔方世界的全部力量。
就像无意中闯进幻境的爱丽丝,或者初入迷宫的玻利瓦尔,塔洛表现得手足无措,又正是这种天真纯粹的局促不安,让塔洛无意识地尽力嘲讽和解构着模块结构所展现的一切,从这里开始,记忆、习俗、爱情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政治——这些加西亚·马尔克斯寓于魔幻的现实语境,一一复现于因塔洛而转动的魔方世界。
作为观众将以此获得另一层的游移、揣度、怀疑以及不安:黑白的影像显露着意义,却又遮蔽了表象,并且二者最终混沌之际分裂出多维的场域。
塔洛的魔方,是将近三十年中国社会结构变动过程经由时间压缩后进行的流态呈现,这里每一个看似稳定的语境截面:二代身份证,照相馆里的固定背景、姑娘的爱情与背叛,小镇的周期性日常、草原上的羊群……都隐含着无穷可能的变幻组合,这种“变动扭曲”的时空,有着“超越现实”的无比真实,是黑白色的毕加索与达利,冲击着观者无尽的想象,比蒂姆波顿的世界更加瑰丽。
如同影片里反复出现的镜像呈现,无限空间的延伸感,亦虚幻了时间的无尽性。
“一切的现实,实际上都比我们想象的神奇得多……现实是如此匪夷所思,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无论诗人或乞丐,战士或歹徒,都无需太多想象力,最大的挑战是无法用常规之法使人相信我们真实的生活。
”(加西亚·马尔克斯)没有起始,亦无最终,许多人或许习惯性将塔洛看作又一个虚构的悲剧性生命,随之从中获取个体对于时代的无力,然而无法否认的过程中的塔洛,在魔方世界充满未知转动中,获取了异常丰富的存在性体验:新奇、迷惘、挣扎、抉择、幸福、悲哀、拥有、失去……人世间的百般滋味,他在极短的时间逐一品尝,这究竟是不幸还是万幸?
走出了自我王国的塔洛,如果说还有什么让人意犹未尽的话,那么必然是开放式的结尾?
or起始?
留给观众一个依然黑白叠合但可以选择的人像:是警务室失神木讷的游魂?
还是荒原中迎风饮酒的牧人?
现在,你可以继续用思维转动塔洛魔方,掌握一次他人命运投射到自我生命的机会:塔洛(我)是会哀痛沮丧地呐喊:“我什么时候能走出这个迷宫呢”,又或者,塔洛(我)会憨厚潇洒一笑:“生命中经历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怀想此事时,能记起些什么,又会如何看待。
”两句话,皆来自加西亚·马尔克斯。
正如马尔克斯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神奇或魔幻只是每日可见的事实,万玛才旦用《塔洛》这部看似虚构的新片,持续着自己一如既往的现实主义本土关怀,在捕捉生命原初状态的同时,他用黑白之色打破着现实与幻象的界限,阿巴斯式的影像语言之间,我们能参悟到那种经典的人性之问:我是谁?
我来自哪里?
要去往何方?
”塔洛用看似平和的犀利眼神,代替我们观察这个世界,导演在简洁的黑白镜语里,创造出一个克制而不断流动的影像文本:不紧不慢,从容冷静,削去波峰,抚平低谷……富含韵味的细节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无所畏惧。
沉浸在个人与社会、历史、道德关系纠缠的观众,将在一个统一的普遍性的哲学命题找到共鸣。
没有答案,但是我们如同塔洛,在转动不息的魔方中寻找不确定的未来。
“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孤独的症结所在。
”(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朽的孤独。
——仅以此纪念万导
2 ) 黑白影像,固定的长镜头。
乍看之下是那种原生态的电影,看下去你会发现并不是,万玛才旦相当的学院范儿,完全就是在按照主流类型片的写法在做这个独立范儿的剧本,而且文本非常的细腻,各种隐喻的隐射的符号化的东西都是聪明的半遮半掩,就连藏族人的精神现状也是带有留白式的开放,以一个人见两个民族,完成度很高。
城市社会于塔洛的双重洗劫。
踏入社会建立身份标识就像是“还俗”仪式;而女性的侵入则又带来着巨大的诱惑与不安,从而被卷入孤独境地。
毛语录的诵经化,KTV与藏摇Live现场,酥油灯式的照相馆等,以黑白影像、固定长镜头折射当代藏人的精神境遇,前半段隐现的温情更是加深着后续最终的迷茫无措。
背语录如诵经,无身份即“坏人”。
十六万剃个头,心一动梦已空。
黑白影像,早早确立了二元对立和形式冲突,如生死,轻重,好坏,单纯与复杂,原始和现代,小辫子/塔洛,牧羊人/理发妹,荒野/县城……抛开这些意识上的先行,从影像美感来说,的确是个人最喜欢的一部万玛作品。
对镜子的反射,还有KTV的LED射灯印象最为深刻。
人的内心感情,有时候真的不需要言说。
摄影真的就是“修女艾达”,大量长镜头,黑白影像,只留一个人头在画面底部,自传体,孤独和暧昧…可看性更强,西藏背景也更有代入感。
为自己受苦,为人民服务。
黑白画质过滤多余情绪,固定长镜头冷静而五味杂陈,没有身份的孤独牧羊人,进城办身份证,遇见多情发廊女,情窦初开像吃禁果,心似沸水,不能再自由地守护羊群“为人民服务”,剪发、杀羊、拍照、背诵、骑行,道阻且长无法回头。
原来藏族姑娘不喜欢古老情歌,只爱听嘻哈风格新藏歌,她不爱人只爱钱。
3 ) 若没发现世界的此般变化 无数个夜也不会如此寂寥
塔洛离开县城的时候,买了50个鞭炮,我在看时还很不解,以为他是帮别人带的。
可我忘了他只有羊。
漆黑的夜,连星星都没有,只有一个不够圆的月亮;五十个鞭炮,三盒火柴,组成了千万个寂寥的夜——塔洛在深夜点燃鞭炮,冷不防的成了最触动我的一幕。
不用说,塔洛是极其孤独的,草原成了他和羊的孤岛,但我仍记得在片头,他一边喂着小羊,一边背诵着《为人民服务》的样子,他那时还会笑着,他还会对局长讲自己放的羊,如数家珍。
他说,放羊也是为人民服务,我死了也会重于泰山吧。
直到他从照相馆的背景图上知道了,除了拉萨,还有北京天安门和纽约自由女神像。
直到他见到了第一个剪了短发、还会抽烟的藏族姑娘。
如果没有发现这个世界在发生着此般变化,无数个夜也不会显得如此寂寥。
最孤独的,莫过于发现孤独。
身份证是只有活在现代这个陌生人社会中的人才需要的通行证,办理身份证的过程,让塔洛发现了这个社会,然而他始终未能拿到这张通行证。
羊都卖了,他回不去了辫子没了,他只能做之前一听见就想发笑的“塔洛”了钱财丢了,那个曾经许诺要带他去拉萨、北京的人,带着塔洛迈入现代城市的希望一起消失了那辆开不走的车,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他尴尬的停在半路,哪都去不得。
有趣的是,电影中没有交代他骑着那辆车究竟是往城里去,还是往山里去,其实这已经不甚重要了,因为对于已在路上的塔洛,面对着意外出了故障的车,无论是城里还是山里,在那一刻都显得遥远得无法到达。
他大概不会明白,为什么在他有着辫子的时候,可以是“小辫子”,没有辫子的时候,连“塔洛”都不像了,还非要重新去照证件照。
在他再次背起《为人民服务》,表现的十分窘迫局促时,我才发现他已经很久没有在片头的那种笑容了。
其实看到最后的时候,我一直在等待着那个爆发,也特别害怕那个爆发,很怕会破坏整个电影都保存下来的那种克制的孤独的美感,我害怕歇斯底里、大喊大叫,但默默流泪在此时似乎也会是无济于事,所以到了片尾我也很迷茫,我甚至不知道我在期待什么。
塔洛是一个疑问,是无论是生活在此处还彼处的人都无法解答的疑问,我甚至不愿意称他为悲剧,因为若称为悲剧似乎也算是有了一个结论和交代,而看到最后,这结局依然让人无所适从,那声鞭炮,从不是终结。
4 ) 明知没有结果,可我还是要来
我叫小辫子,是个牧羊人。
虽然我的真名是塔洛,但几乎没人这么叫我。
我习惯戴着宽大的帽子遮盖头发,习惯带一只小羊放在包里,习惯一个人,习惯没有身份证,习惯没有人知道我的每时每刻。
所以在遇到理发店女孩时,我一度觉得她是个骗子。
然而她的靠近还是让我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感情,她说要去拉萨,去广州,去上海,去香港,我说,那我们去美国纽约吧。
和她分别之后,日子开始变得漫长,就连呼吸也寸步难行。
曾经习惯的一个人的日子此刻变得如此艰难。
“我见过天地,也算见过众生,但从没见过自己。
”从前,活着的意义就是生存。
现在,这意义我却不再找得到。
群山、羊、稻草人还有“人必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不是我的群山、羊和稻草人。
我所拥有的只是一根辫子,一顶帽子,和一只羊。
羊群的叫声渐渐淡去,震耳欲聋的嘶喊不再有意义,坐在这里的一刻,我告诉自己,试试吧。
虽然她是个骗子,虽然她唱歌难听的要死,但是她是唯一一个靠近我的人了。
可能不会有这么糟糕,试试总不会怎么样。
我把羊卖了,拿着十几沓钱去找理发店女孩。
我看到她眼里的狂喜和贪婪,却没看到我自己。
帽子拿下来,辫子剪了,身份证也办好了。
我终于不再是游离在外的边缘,可我也从未感到如此得轻。
-“每个人都很重要,你是个牧羊人,你也很重要,如果你现在死了,你也是重于泰山。
”-“恐怕现在我死了就轻于鸿毛了。
”-“那个警察问我有没有身份证,我说没有,他以为我是个小偷,看着不太像个好人。
”-“你现在像个好人了。
”
万玛才旦是个对称狂魔。
影片开始时被拘束在框中的塔洛呼应结尾时被排除在框外的塔洛,“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字从一开始的正写变成镜像排列,“公安”二字从模糊变为清晰,都在暗示代表藏人青年的塔洛从未摆脱游离的境遇。
他永远不会懂好人与坏人为什么用身份证来辨认,生命的轻重又为何被头发左右。
辫子失去了会再长回来,那关于这个世界呢?
如果我从未拥有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什么时候能拥有我?
大地苍凉,不管我走了多远,总也走不出充斥羊腥味的草原,走不出空无一人的荒地,走不出没有人等我的理发店,也走不出我的心。
踌躇天地间,忽复无所意。
也许总也找不到自己,但也只能止步于此了。
5 ) FIFF16丨DAY4《塔洛》:迷失在原始与文明的分界线上
第16届#法罗岛电影节#无人知晓单元第4个放映日为大家带来《塔洛》,下面请看前线纯朴藏民融入世俗洪流的评价了!
迷幻松饼:不错,摄影构图我喜,但有的镜头太长。
zzy花岗岩:尘世里走一遭,生命便轻的不能再轻了。
曲有误:镜子里,他是塔洛,镜子外,他是小辫子。
热可可加盐:真诚且新颖,黑白的质感和对于身份的探索相当有意思。
赵小毯:文学性和影像塑造上都有所建立,身份认同的触感孤独地延伸。
Spy Liu:藏民在现代化中的“迷失”,个人感触不多,但文本和形式都不错。
非有想非无想:人的成长、身份的认同,乃至整个社会,族群的成长,身份的认同都要被“骗”的倾家荡产一无所有才能达成,也是悲哀。
Xavier-耐观影:对于缺爱的人来说,你给他的看似微不足道的一点点余温都会换来他竭尽所有近乎他整个世界的回报,此时一切理性判断和系统认识全部失效。
Her Majesty:万玛才旦的文字是极简的,仅剩下动词和名词;而当他把文字转化为影像后,则显得有些冗余。
可能《塔洛》想要的东西太多,把导演的美学和经验挖掘得过多,所以在其后两部作品中他再也找不到话想说。
Pincent:藏民牧羊人的生活,原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无身份证”是藏民自我身份认同的迷失,现代化与外来冲击过程中善良淳朴与拜金主义的矛盾,两次背诵毛主席语录的讽刺效果,黑白摄影很漂亮,人物总是在镜头边缘。
欧.尹:极具作者风格的固定机位长镜头与黑白影像,开头长达十二分钟的为人民服务的背诵看似简单,实则蕴含了充分的延展与解读空间,与结尾呼应,保证了本片较高的完成度。
然而就我个人观感而言,承担着刻画人物精神状态任务的核心段落,即中段塔洛从城中归来后的部分反而有些出戏。
可能这样的电影只有在电影院看才真正有其价值。
psychopath.MN:听不惯说唱,只会唱伊拉。
吸不惯新烟,只愿吸卷烟。
从一口气背下语录,到无法背下去。
从正写的“为人民服务”到变成镜像的反写。
来“人间”一趟,为了身份证而回忆了自己是“塔洛”,却又迷失了自我。
留了一生的辫子,今后不再留。
以为是爱,那个说“自己知道自己是谁不就行了么”的他或许此后再也认不出自我。
失了自我的“真”,被新世界唤醒,或许是必然。
布谷卟咕:一个很简单的关于文化流失,身份迷茫的故事。
节奏很慢,虽然银幕上两人之间的化学反应很有趣,但看了故事开头能猜到结尾。
对身份思考的呈现有些流于表面,强调对立,感到片子里充满了焦虑而没有根基。
导演是想通过拍摄来进一步解答自己的疑惑吗,还是他心中已经有一些观点?
如果能在拍片过程中一层层剥离,一步步深化问题,不像现在这么工整的话会更讨喜吧。
警察局的问答很有意思,温和的有一搭没一搭地通过在观众看来略显尴尬的氛围中呈现出双向交流的失败。
鲍勃粥:最原始的藏族力量全然失语,起点已经是革命力量与经文的混杂,然而抵挡不住如“二代身份证”的更新,终点是崭新的魔幻现实主义,对外界的肤浅理解和似有似无的链接(照相馆背景的北京和纽约,说唱表演等)。
塔洛内在身份是封闭的,外在身份逐渐被重建,头发剃去,在新环境的无力(爱情与城镇是相通的),镜子中的人物模糊,烟雾缭绕。
黑暗的苍凉地貌上的浊酒独饮与二踢脚是为逝去的草原灵魂送葬。
塔洛与局长被烟囱隔开,与女人被镜子隔开,构图已将他孤立无援。
羊死了,死了的却不只是羊。
#FIFF16#无人知晓单元第4日场刊将于稍后释出,请大家拭目以待了。
6 ) 【阿若博巴】一为藏人影迷对《塔洛》的解读
阿若博巴|| 一位藏人影迷对《塔洛》的解读作者:@霍儿登达 摘自微信公众平台:阿若博巴不喜欢被定义的粉丝 去看《塔洛》的前两天,我突然开始抗拒它。
原本我是很期待它的,但后来我被莫名其妙地拉进了好几个组织观影的微信群,让我有些被信息轰炸的感觉,滋生了一些小情绪,于是我把气撒在了电影上。
事实上,我不需要谁提醒,涉藏的电影但凡不是《天上的菊美》这种听名字都能让人产生误会的肉喇叭手笔,我都会去看,再者,我跟塔洛一样,不接受别人定义我的身份,我讨厌被情怀,就像塔洛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要被颁发一张身份证。
看完这部电影,我想写点儿对这部电影很主观的一些感受。
我不把这篇文章称为影评,是因为我的资历离影评还差的很远。
暂且叫它观后感,只当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感受。
因为是个人的感受,所以我的看法离电影本身要表达的内容或许大相径庭,倒也罢了,我只负责记录因这部电影产生的一些想法,无意冒犯或揣测,也因为是个人的看法,我不会做流水账像毒Sir那样蹭IP,我不刷图片,不插表情,我只想庄重而严肃地,干干净净地就像塔洛的画面给我的感觉一样,向您讲述我眼中的《塔洛》。
有关身份认同的引子 刚说到塔洛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要去办身份证,电影的开篇无疑从一个有关身份的话题展开,开篇就很明确地告诉观众,这是一场有关身份的戏。
曾经的牧羊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的身份定义已经不足以概括他是谁了。
人们叫他“小辫子”,可现在他需要一个代表着权力的所长认为是真正的名字的名字---塔洛。
塔洛这两个字蕴含深意,在藏语里“塔”是“逃脱”的意思,不是“逃离”或者“逃跑”,而是“逃脱”。
塔洛在影片中有两次提到:“听到别人叫我塔洛,我就觉得可笑。
” 他觉得可笑是情有可原的,明明逃不掉命运的安排,却偏偏起了个名字叫“逃脱者”,讽刺之意,不言而喻。
而塔洛要领取自己被给予的身份,他理解也好,不理解也罢,历史由不得他和像他那样的人理解或不理解,跨出派出所的门,他便踏上了一条认命的路,这一路,他是去领取一张证书,也是去面对命运对他做出的安排。
被夺去色彩的人生 电影一开始,塔洛便在派出所用一种本该属于虔诚佛弟子为六道众生脱离苦海而诵经的调子念了一段“为人民服务”。
两种毫无违和感的元素被强行兼容,塔洛身上传统文化孕育的习性在此处被现代文明活生生地强奸。
这一幕开篇,便在一个没有色彩的黑白画中开始展开。
这部电影一开始便夺去了颜色。
想想一个被强奸的人生,余下的生活是否会像是活在阴影里呢?
塔洛被动的命运,本就没有颜色,就好像今天生活在雾霾中的我们一样,我们人生的初始设定是没有色彩的。
黑白色调给人的压抑感,无时无刻不烘托着塔洛隐隐和命运对抗时的无力感,和他注定苍白的人生的绝望情绪。
整个故事,便如此在没有色彩的叙述着塔洛苍白无力的过去和现在。
黑白化的处理,让很多人会觉得是较为省事儿的一种做法,但看过电影的构图,几乎每一个镜头都有一种湿版画一样的风格,我觉得其实这种处理并不省事儿。
重要的是,它与影片的意境较搭。
一场与“现代性”的较量 塔洛从所长处领命,踏上了接受自己身份的路途。
骑上他的摩托车,带着他的小羊羔,来到县城。
一进到一个被“现代化”侵蚀过的小县城,他便在县上的任何角落都显得格格不入。
他的身上流淌着一个民族留下的谦逊与克制,可在这里,他的这些本来应该被赞美的品质却愈加显得笨拙和可笑。
他就像这个时代冲刷下的藏人,是“现代性”眼中极其不协调的存在。
电影在塔洛进城的这段章节中列举了许多文化符号之间的冲突。
首先是照相的那一对夫妇,背景在拉萨、天安门、和一座城市之间切换。
在照相师德吉比较现代化的标准下,他们的藏袍必须换成西装才配得上背后的城市。
摩登的德吉嫌弃他们的传统服装,然而却只有抱着羊羔他们才能从容,或许唯有将牧人的文化符号归还于牧人,他们才会安心吧。
强迫他们走上一个并不符合自己的舞台,叫他们如何是好。
塔洛进入镜头之中,被德吉深深的嫌弃,嫌弃他的小辫子、嫌弃他的包、嫌弃他因无所是从而略显僵硬的举手投足,包括他的笑。
唯有他经历一场“洗礼”才能被“大头照”接受,而为他进行洗礼的这位女子,也让塔洛的人生开始跌宕。
能够让骗局结出果的女子 两种文化的冲突,照相馆延续到理发店。
理发店里,一位不符合传统女子标准的女孩儿,她一头干练的短发,还会抽烟,一副久经社会的面孔。
从塔洛细数自己的羊群开始,便处心积虑地一步一步将他吞噬。
她带他去唱歌,而他却只会唱一首拉伊。
他因为女孩儿的烟味儿和啤酒呛的咳嗽,而想要唱流行歌曲的她,为他买了他喜欢的烈酒。
两种不一样的歌,两个不一样的人,两瓶不一样的酒,中间隔着藏人的过去和“现代性”,在这件小小的KTV包厢里,相互对抗,而对此两位主角对这场较量却并无感知。
此时,背景里隔壁包间里一名男子歇斯底里地嘶吼着根呷的那一首《拉萨酒吧》,“因为我是个没有钱的人!
”。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便传唱有关物质决定爱情的真理。
塔洛身上的文化也在渐渐地被挤兑和吞噬。
她用火一样的热情在塔洛心中种下了爱的因,却无意要结出恋的果。
然而对影片而言,她像一根穿在珠子之间的线,为塔洛接下来变卖羊群,回到县城做好了铺垫。
我并不认为这是一部有关爱情的电影,更多的是一个有关被诱骗的故事,而如果把杨措扮演的虚情假意扩展至整部影片,塔洛从所长那里,一开始就被命运所欺骗,杨措,只不过充当了让这命运的骗局最终结出果实的女子。
真正属于自己的领地 荒山野岭,守着羊群,伴着狼嚎,那是牧人原来的样子,就像是夜幕下那一只藏獒浑厚的咆哮,白天主人端着碗盆喂它,它友善地摇着尾巴,那才是一只藏獒原来的样子一样。
它一口一口喝水的声音不知道能够激起多少藏人记忆中家门口的那只猛犬。
在这里,没有人会怀疑塔洛的身份,也没有人会要求他拿出证明。
他是个牧羊人,人称小辫子,是个名副其实,毋庸置疑的牧人。
在他被命运驱逐前,原本属于这里,这里是他浑然天成的归属地。
放羊的生活如此简单,却因为他惦记一名女子而宿醉一场,使羊群遭狼袭,还挨了两记响亮的耳光。
那一晚,牧羊人在小土屋里炖了一锅羊肉,热气升腾,在透过小窗户的射进来的光线下显得安逸而又温暖。
塔洛用他的匕首各一块羊肉放进嘴里,再喝一口烈酒,那一幕,塔洛显得自然而和谐,没有丝毫的不协调。
在放羊的山头,塔洛与羊群之间在电影画面上构成的和谐图案,与之在县城的格格不入形成了对比。
谄媚的歌颂者 塔洛便卖了羊群,又来到县城,一步一步走向妥协。
原来定义它身份的小辫子,也在这位女子的怂恿下给剪掉了,她就像命运派来的奸细,不经他同意,也没有给他反抗的机会,在自己毫无退路的时候他的反抗早已无济于事。
他能做的,就是克制和顺从。
塔洛本想为她演唱自己在放羊时学的三首歌,被女孩儿拒绝,替代他歌曲的,是去听一名歌手的演唱会。
他无力拒绝,也无力反抗。
事实上,塔洛还并不适应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人在咏唱了。
酒吧里,这位饶舌歌手,唱着塔洛陌生的节拍,众人像是加入了邪教组织一般地亢奋,挥舞着双手跟着摇摆。
塔洛在这种极其陌生的节拍里开始无所适从,他对这样的音乐没有共鸣,也无法理解众人的亢奋。
而这样的音乐,就像根呷的《拉萨酒吧》,早已脱离了藏歌原来的样子,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冲击,藏人的音乐在不断地的改造,努力像流行靠近。
酒吧里的歌者,像一根舌头,在跪舔着“现代”这位嫖客亮在他眼前的新标准。
绝望的“逃脱者” 最后的塔洛,那位名不副实的逃脱者,站在路中间,进退两难。
他剪掉了辫子,卖掉了羊群,甚至记忆力也不如从前了,再一次踏上办证的不归路,却早已不是那个曾经留着小辫子,言行中略带谦卑的牧羊人了。
他被命运伤害,站在前行的道路上不知何去何从,他已经没有办法回头去做一名牧羊人了。
然后再往前,等待他的又是什么。
除了绝望,我们还剩下了什么?
文章末端,我们回到开头,在我文章还没有写完的时候,我在微信上收到几个群的提示:你被“某某某”移除群聊。
我的微信在不知不觉中默默的经历了一场浩劫,它就像一个被传统遗忘的女子,被现代化这个土匪拽到历史的床上,不由分说地接受轰炸。
然后在被消耗完毕以后,也无需对你做出解释,我如同一张厕纸,擦拭了他人的快感后被丢弃在历史的垃圾堆里。
这场结束,犹如塔洛的结局一样,那样突然,毫无征兆,让你不知所措!
7 ) 导演的一些话在映后交流会上
第三届浙江青年电影节的开幕影片就是《塔洛》,映后交流会上Q&A环节导演的一些观点,不是原话,就是大概记了一下。
1 塔洛能完整地背诵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 这些话(比如里面讲好人的死重于泰山 坏人的死轻于鸿毛之类的)像是他的宗教;
2 选用黑白影像 因为塔洛的世界kind of非黑即白 他对很多事物的判断也是如此;3 理发店的杨措让塔洛多学几首情歌 剧本里本来安排有个牧羊女教他情歌 但是后来去掉了 因为塔洛是孤独的。
所以 此后在山上的场景设置也几近极致 塔洛都没遇到其他的人;
4 影片里很多场景背景噪音都很大,因为导演觉得 对于藏区来说 那些噪音也是真实的一部分;5 在很多县城的画面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框 因为在山上的时候塔洛是比较自由的状态 但是下了山 他就不自在 所以在很多画面中设置里框或者是塔洛会处于画幅的边缘;
6 理发店里很多都是镜子里的像,暗示塔洛与理发店女老板的的关系是虚幻的;
7 摄像机都是固定机位 主要是希望形成一个冷静的视角 ;
其他记不得了……总之是一个值得一看的电影,因为导演是个谦虚(not 谦逊)但是有原则不妥协的人(比如对于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他报以“不屑”但是礼貌但是又超级简短店的回答),是一个有哲思的人应该
8 ) 薛定谔的万玛才旦
薛定谔的万玛才旦对我来说,《塔洛》是一部关于“初恋”的电影,它讲述了孤独的牧羊人塔洛为了“爱情”背叛自己的故事。
可是万玛才旦显然不满足于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
为此,他挖空心思地设计了一系列符号化的隐喻,并将其精心地安放在影片之中。
他企图通过对人物际遇的书写来完成自己指桑骂槐的目的。
他就像一个隐藏在影片背后阴损的偷袭者,时不时地突然出现一下,用他不高明的拳法冲着观众一顿乱捶。
就算作为一部“概念先行”的电影,《塔洛》也是不及格的。
万玛才旦令人遗憾的计算方法,把他原本不算糟糕的“概念”公式——“人在寻找身份的过程中丢掉了自己的身份”——运行地支离破碎。
人物在片中的行为动机混乱不堪,导致了他们行为的结果没有任何意义。
在这部电影中,我看到了一个薛定谔的万玛才旦。
杨措对塔洛到底有没有感情?
如果有,为什么抛下塔洛?
如果没有,她又为什么給塔洛剃头?
答案很简单:杨措对塔洛的感情是既有又无的,同时存在的。
导演对“戏剧效果”的追求,决定了杨措对塔洛这种扭曲的爱。
因为对于导演来说,塔洛必需要被抛弃,也必须要剃头,只有如此这般,才够惨,才够艺术。
9 ) 近乎离题
鉴于豆瓣已经有很多影迷细腻走心的分享,这篇影评不会针对电影本身描述太多,本来也没想写,看完以后不禁想起我见过的藏人,如果你不介意离题,可以往下看看。
这部电影是在看幻梦墓园前的预告片时在意到的,那是整个亚洲太平洋电影节的预告片,虽然只插了几个镜头,但印象深刻,黑白极简,构图舒适,台词有趣。
回到家在网上看了整个预告,主角咏叹似地背重于泰山轻于鸿毛,再加上陆支羽的倾情推荐,下定决心要去影院欣赏。
进场的时候只有我一个观众,我很惊讶,志愿者姑娘说可能你来太得早了,她告诉我这是一部很美的电影,我当时对它还不甚了解,默默地质疑美是否是个准确的描述。
我告诉她我认识一个专业影评人把它列为年度十佳,她感叹,继而点头:我确实觉得这部电影非常棒。
她说得没错,这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故事,写实冷静,颇具纪录片的气质,简洁而粗犷的摄影风格,感受得到导演在台词画面细细琢磨的诚意。
有时看塔洛抽烟时会听到烟草嘶嘶的燃烧声,感叹果然看电影还得是电影院。
我去过西藏两次,自认为是心态开放体验至上的旅行者,所以感受很复杂,虽然我没见过塔洛这样的牧羊人。
第一次进藏走的丙察察,沿途景色自然不必说,一起搭车的是两个藏族小伙,他们把松茸馅的包子分给我吃,他们说话的时候不敢看我,脸却朝向我,习惯在每句话最后加一个嘛,但是没有故作亲近的意思。
他们为颠簸的土路感到羞愧:我们这里路很差嘛……我苍白地安慰他们,城市里堵车也很麻烦。
其中一个话多些的告诉我,几年前有剧组在这里拍一部叫做康定情歌的电视剧,里面有个女演员是苏州人,她很漂亮的嘛。
这是他对苏州的所有了解,这也是我听过的对苏州最为特别的定义。
到左贡时天已经黑了,有一家叫做大炮饭店的在营业,两个扎西以主人的姿态颇有派头地要来菜单然后点头哈腰地递给我,你点嘛。
第二次进藏坐的上海出发的火车,车厢被将要回西藏过新年的学生和生意人挤满了,那些年轻的学生除了口音和容貌已经分辨不出他们是藏族人还是沉迷于嘻哈音乐的韩国人,他们大声地放着音乐唱着歌,享受着来自别人的注意。
夜间经过一段海拔奇高的地方,估计是昆仑一带,车舱之间全是蹦进来的碎冰渣。
我有些高反心跳过快睡不着,索性爬起来准备看星星,有个扎西沉默地坐在窗边一动不动,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担心自己的动静会打扰到他。
和同车厢的拉萨姑娘聊天,她说起藏历新年,坦言不是很喜欢复杂的礼仪,宁愿待在家里睡觉。
路上经常会看到向经过的火车立正敬礼的边防战士,过高的海拔和强劲的风让他们无法站稳,他们的战栗清晰可见,我忍不住感叹,真是辛苦啊。
那位藏族姑娘扬着眉毛说他们工资很高啊。
我想我当时看她的眼神一定是难以置信的不满。
不过她多次重复一定要去北京天安门看看。
到拉萨站时已经很晚了,火车站外面仍挤满了接寒假归来孩子的家长,他们自觉地让出了一条道,被他们拥着会产生被热烈欢迎着的幻觉。
在去青旅的出租车上不由感叹拉萨的开阔和道路的干净,司机说,是啊,不像你们内地啊,又脏又乱的嘛。
他的口气不容置疑让我难以反驳,接近城中心的时候,一眼瞥到金碧辉煌的布宫,我不禁啊了一声,司机很得意,不要激动嘛,有的是时间慢慢看,这可是西藏的大宝贝嘛。
我脱口而出,这也是中国的宝贝。
他直摇头,中国是中国,西藏是西藏,你们是内地,我们是高原,不一样。
我不置可否,总之是宝贝就对了。
到了平措,司机像是整理衣服一样整理好我的登山包,架着帮我背上,我向他告别:扎西德勒。
在布宫前的广场上看见许多同样远道而来的藏族人穿戴整齐地留影,面对镜头依然有那种几十年前独有的肃穆感。
大昭寺醒得比太阳还早,清晨六点就已经挤满了磕长头的人,这里有更多长期驻扎的藏民,不停行礼的或者只是晒太阳闲聊的。
我没有在塔洛里看到很多以针砭时弊自居的电影里一贯咄咄逼人担当坏角色的警察,我向便民中心的警察问路,他们的态度好得出奇,非常详细地指示方向,一边目送一边问要不要送你去啊?
暴走得太累,在布宫广场上直接坐了下来,一个警察立马走过来说,这里不可以坐哦,语气很和蔼。
我不是来静坐的。
我说。
他笑了笑,我知道,但是地上冷。
绕着八廓街转的时候给一位乞讨的扎西零钱,一群人冲过来暴力地把我手里的钱全抢光了,当时的心声是WTF。
遇到一个小女孩,一头羊角辫使她显得怒气冲冲,她自言自语地对我笑,跟我同行了一段时间,后来被人群冲散了。
再看见她的时候,她近乎欣喜若狂地扑了过来。
我指了指相机,她却笑着摇摇头。
看到一个藏民错误地估计了经幡的厚度一头撞进去时忍不住笑了,接着感觉到来自人群的恶意目光,急忙躲进厕所,排队时仔细地翻着相机的图,旁边的藏族大妈小心翼翼地注视着相机屏幕,我觉得她很可爱,一张张解释给她听,也不知道她能不能意会。
在仓姑寺和一位藏族母女拼桌喝茶,突然旁边的藏族大妈抬起了我的茶壶,你拿错了吧,几个字都到嘴边了,看她很用力还是拧不开,我接过茶壶一拧,挑眉示意:力气大吧,她开心地惊叹起来,拿过茶壶把我的杯子满上了……去樟木的路上,藏族司机把他带着的自制奶酪分给我们吃,说,吃这个就不会高反了嘛。
司机会很得意地介绍一座座山,就像素未谋面的老友一样,经过竖着各种事故多发悲惨指示牌的山口又严肃大声地念些咒语,吓得我忙正襟危坐起来。
偶尔和一些坐在敞篷拖拉机上裹成球的藏民擦车而过,很难想象他们要怎么到达目的地。
聂拉木是最后一个境内的检查站,晚上十一点接近凌晨到了这里。
当时,检查证件的工作人员坐在敞开的帐篷里,我都替他们打颤。
和司机分别的时候,我问他,你应该去过尼泊尔吧,一直走这条路线嘛。
他难为情地笑笑,没有,我们不能出国的嘛。
藏族嘛。
我无由来地满怀歉意起来。
在尼泊尔费瓦湖边闲逛时和一个摆摊的老头聊起天来,他说他们一家当年从拉萨逃亡而来,父母都被打死了,他比对了一个狙击的姿势。
你知道……这是谁干的吧……我无由来地脱口而出,真的……很抱歉……他笑着说,这和你没有关系啊。
在一家西藏人开的工艺品店里和店主闲聊,这位扎西换成中文说,我煮了一些热茶,喝一杯吧。
我当时赶时间去办徒步的手续,只好谢绝了他的邀请。
另一个藏族后裔告诉我他想回西藏,真正的自由的属于他们的。
我告诉他我刚从西藏过去其实西藏现在没有那么糟糕。
这些是我遇到的西藏人,也许他们有过和塔洛一样的尴尬,也许有更多的人去县城走了一圈,去东部走了一圈,去大城市走了一圈,整理思绪,想着,啊,我还是回到我的羊圈去吧……看完电影我瞥见一个端着高深莫测笑容审视全放映厅寥寥十几个观影者浑身散发快来跟我聊塔洛气息的亚洲老头,我终于知道那从背毛泽东语录开始的不绝于耳的哼哈恶意嘲笑声是从哪里发出来的,我想他没有理解塔洛。
10 ) 塔洛:现代社会的“迷途羔羊”
电影最后,塔洛向派出所所长直承自己的“坏人”身份,坦言将“死得轻于鸿毛”之时,电影最开始那位要“为人民服务”、将“死得重于泰山”的牧羊人已经自食其言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剪掉了辫子,前往派出所领取证件的举动便被宣告作废;不管是“好人”塔洛还是“坏人”塔洛,最终都没能获得现代社会的身份认同。
<图片1>我们应该来细致分析一下在电影开头与结尾,特意营造的对比。
一开始塔洛留着具有象征意味的辫子,张口即来毛主席语录,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死得重于泰山”,而至结尾,同样是这位塔洛不仅失去了具有身份象征的辫子,在背诵语录时出错,同时卖掉别人委托他放牧的羊、危害了公共财产,他将“死得轻于鸿毛”。
这一变化是非常显明的,通过一个更具象征意味的行为——办理身份证——所贯通。
无论是电影里中的社会,还是现实社会,身份证都被认为是用来确认个体身份的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证明。
有了它,塔洛便不会被照相馆门口的警察巡查,他也能像别人一样去到像拉萨或北京这样的大城市。
塔洛需要办理身份证,也必须去办,我们需要看着他一步步地落入现实社会的罪恶深渊,看到他如何遍寻不着自己的身份。
而这,正是导演为电影设定下的坚实逻辑。
如果塔洛不去办理身份证,他就没必要上县城去照相馆拍照,也就不会为了面容整洁去洗头,碰上那个将骗走他的钱财的洗头妹,自然不会落下 “坏人”这一盖棺定论。
电影通过这种简单又缜密的因果联系,将一个普通的牧羊人抛进现代社会的漩涡之中,看他举动,看他挣扎。
当塔洛最终从漩涡中走出,他发现的是自己的人财两空:他不仅失去了仅有的财产,同样失去了“好人”的身份。
<图片3>为什么一个普通的牧羊人会被堕落进现代社会的罪恶之中?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们只能借助影像本身去寻找。
一开始,在照相馆中出现的那三个拍摄背景:分别是拉萨布达拉宫、北京天安门、纽约自由女神像,已经为之后的一系列发展埋下了伏笔。
对于这位终身牧羊的男人来说,这三张图象征着对另一个世界的全部想象。
首先是布达拉宫,塔洛作为一个藏民身份对其形成的崇高想象(宗教),其次是天安门,因为从小背诵的语录中反复出现而成为“朝圣”之地(政治),最后是自由女神像象征着美国梦所代表的全球化浪潮对一个西藏偏远县城的冲击(经济)。
这三种想象为塔洛画下了一个圆圈,框住了他,同时等着他往下跳。
故而,当塔洛坐在理发馆里,面对既青春又漂亮的洗头妹的“勾引”,一种从不曾唤起的“情欲”起了作用。
也许是爱情,也许不是;也许只是两性相吸的自然冲动;再加上从女孩口中所泄露的外面世界产生的“诱惑”,并通过在KTV唱的“拉伊”催化成熟。
我们不能一口咬定塔洛对女孩产生了爱情,同时这份爱情导致了他的出格举动。
这过于绝对,人的行为往往是通过一系列不明缘由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得说,塔洛也不例外。
从塔洛身上,我们看到两种力量间激烈的冲突:一种是被从小规训的“为人民服务”的人生宗旨,一种是现代社会向他发起的“罪恶”勾引。
当塔洛第一次从城里回到派出所,将拍好的照片交给所长之时,他有点茫然地提到:自己遇到了“坏人”。
很明显,他所说的“坏人”指的便是那位企图诱惑他卖掉羊,拿着钱一起远走高飞的洗头妹。
但这种声明却是以一种模糊的方式发出,从中我们便看出塔洛在两股力量间的摇摆。
这一行为也可以看成是塔洛的潜意识中社会主义价值观对于资本主义价值观压抑而未完全胜利导致的自然结果。
<图片4>引发塔洛真正走向“罪恶”的还在后头。
在一次为了抑制咳嗽,喝下一瓶白酒后,塔洛便沉睡不起,导致放养的羊群受到了狼的袭击,死伤惨重;对于塔洛来说,唯一的职责便是:时刻警醒着狼群的临近,一旦发现便要点起鞭炮驱赶。
他失职了。
再加上第二天老板儿子来收羊粪,事情只能被败露。
对于这位终身力行“为人民服务”的“好人”,如今却要被面临“破坏人民财产”的指控,另一种来自现代社会的诱惑无疑开始逐渐往他的内心深处发展,并取得绝对优势。
塔洛发现,自己还可以逃离,也许他想到的是他还没有身份的事实,别人便找不到他。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老实的牧羊人有这种精打算盘的本能。
塔洛最后走向“罪恶”,放弃“好人”身份,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这个无奈之举下,爱情到底占多少成分?
很难说。
当塔洛向女牧民学唱“拉伊”起,我们得说这种爱情已经很强烈了,尤其是这份爱情被外面的广阔世界所升华,成为逃离现实惨境的理想跳板。
<图片5>我们或许还应看到,导演在解决塔洛的这趟身份追寻采取的最终方案。
在电影的最后一幕,塔洛停下摩托车,掏出烟和酒,背对着观众开始品酌。
这里的指意是,塔洛确认自我身份不是通过遵照主席语录所划定的人生宗旨,也不是通过维系现代社会稳定所需要的一张身份证件,更不是借由被唤起的爱情;而是通过对个人喜好的认同。
那烟不是商店可以买到的纸烟,而是手工制作、因为味道太浓而被现代人抛弃的卷烟(演唱会一幕);那酒也不是普通的啤酒,而是味道够烈、也可抑制咳嗽的白酒(KTV一幕)。
通过这两种个人喜好,塔洛完成了这趟对自我身份的追寻之旅。
塔洛虽然失去了辫子,做了坏事,被骗了感情,失去了各种社会身份,但通过对个人喜好的自我确认“寻找”到了自己,作为个体第一次有意识地挺立起来。
<图片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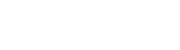





























爱情对塔洛就是一场咳嗽,来了想忍也忍不住;姑娘于生活则是一瓶白酒,倒头喝干酣畅止咳。所长,我遇到了坏人,一个偷光我生活的坏人;所长,我不再是好人,一个丧却了理想的好人。照相馆布达拉宫天安门自由女神像的背景瞬移无比魔幻,现实却是剃刀割断辫子人财两空的嗟叹。而我,重如鸿毛,轻若泰山。
特別精豔!講一個放羊藏民&#34;夢想遇上現實&#34;的有趣故事。鏡頭語言乾淨有力,長鏡頭多而不悶。結尾那一幕特別震撼。今年金馬獎黑馬,望拿下重獎。
傻根受骗记
本来以为是藏版拉扎罗,但比起来实在直白浅显太多。表达上只有大量的固定机位长镜头是唯一让我感到惊艳的。
张献民真是红,都请他做监制。玩身份认同的梗,可惜是次摆拍。
电影本来的样子
“塔洛”的角色在县城部分倚靠各式画面和意识形态的隐喻建立,在回到没有镜像、画框的山里之后,“塔洛”本身的无趣就立马显现。扬措反复无视一个给她十几万的男人想去KTV的要求、拿钱跑路的设计则彻底暴露了导演的偷懒和影片的早泄。
1.万玛才旦主要作品。2.优秀的剧本来源于生活,欺骗的本质就是欲望的交加。此人是何背景,不能轻易而断之。开头的一幕,有一个条框将男主圈住,纵使能流利背诵语录,不能用于生活实际又有何用?3.小羊羔。背景板。为人民服务的本质。听清本音。纯情诱惑。被狼咬死的羊。远眺雪山。黑白胶片。独自饮酒抽烟放炮。
构图漂亮,但是基本上是固定镜头,缺乏镜头内部运动,容易看得疲乏,足见摄影功力还是有限,说个题外话,藏族题材电影不代表就是西藏电影,这电影是青海制造,豆瓣上一群装逼狗在本片底下喊着西藏如何如何,好像自己很熟悉藏族一样,结果连最基本的地区都搞不对,也真是可笑
2024.9.24 洗脑的成功典范
一种镜头外的世界对镜头中世界的入侵。
大概是最近沉迷于革命,欣赏不来这么艺术的创作,也可能这种语法逼近中国现实,造成了暧昧感。事先的二元对立,现代的花招,摆布与留白,在前现代的深情面前,这些形式上的斧凿痕迹一览无余。
期望越大失望越大。过于单薄的人物形象让黑白影像除了形式上装逼之外并无必要,每个画面看上去都想要表达很多东西,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卵用。能让这一切解释过去的就是,导演通过微信连线说的那句——塔洛是一个思维很简单的人。3.5。
太贾科长范儿。一位头脑还停留在前现代的藏民如何迷失在当下现代的西藏,整部电影就是在以极为表面化的符号图解这个概念。再也没有比身份证更直白肤浅的隐喻了。拍得也特别冗长,前面一些二人交流的场景还稍有情绪、气氛的感染力,越到后面越僵硬,画面几乎要凝固成一张张静止的剧照。
自然算很出色的华语电影,但还是不如类似的《修女艾达》。长镜头、黑白影像、简单独特的故事、质朴的表演,独立气质宛然。可是表达的东西无法真正触动到我,只见到原始/现代、纯真/拜金的简单二元对立。身份认同,文化多元这些主题完全可以探讨得更深入有趣,KTV和背主席文章之类还是显得刻意了。
有些镜头不是很必要,比如羊主人后视镜那里。
摄影真的就是“修女艾达”,大量长镜头,黑白影像,只留一个人头在画面底部,自传体,孤独和暧昧…可看性更强,西藏背景也更有代入感。为自己受苦,为人民服务。
塔洛最大的转变来自于他自己无可抑制的欲望,这种无力感虽是我认可的,但总觉得哪不对劲。应该是这种假装真实的做作表达,从故事到影像都透露着一种过份的矫饰。有人说有如阿巴斯,可能只是形式吧,见地差太多。个人觉得万马才旦退步了,这可能和地位的进步有关。
身份证是啥
呆板笨拙,乏善可陈